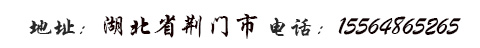孤寂的小站文杨立元诵爱的阳光
|
孤寂的小站 小站像一只秃鹫突兀、孤零地眈视着广袤的原野。百米长的月台上歪斜着几棵桃花树,飘零着几瓣褪尽了芳香的枯朵。道口处的长栏杆涂了颜色,像一条巨蟒时起时伏。一侧有几间砖房,漆成酱紫色,宛如一块发了酵的大块酱豆腐。有一座残破、斑驳的碉堡依偎着它,证明着小站历史的久远。一条长长的河流伴随着两条无休止的铁轨,飘逝在远方。偶尔有一辆火车通过,浓重的黑烟给高远的天空涂上几笔颜色,渐渐地淡化了。一座石桥横亘河面,河那边有百十户人家,在绿柳中露出端倪。这条河叫煤河,原是洋人运送开滦煤的通道,初时是极热闹的,舟楫通行,招来了九省十八县的人,聚成小镇,楼阁林立,人烟密集。蓝眼碧发,挺胸别肚的洋人,漂亮风骚的日本娘们也曾招摇过市,招惹出不少风流韵事,留给后人做为饭后茶余的谈资,消愁解闷的笑料。如今,这条河早已时过境迁,没了往日的风韵,只在地图上添一道蓝色。小镇却依旧飘逸着旧时的遗风,家家门口挂起招牌,杂货摊、小吃部,旅店、饭馆应运而生,有不甘寂寞的好事者开发录相厅、台球室,镇民们从此有了消遣的地方。 小镇上,不做买卖的仅两家,一个是桥南退了休的站长孙头,守着三间空荡荡的房舍,吃着劳保,不图什么,也不缺什么。一儿一女在外,难得回家一次。 另一个是桥北的夏婶,老伴早亡,儿子在外做事,还有一女已婚,留下夏婶守着祖宅。夏婶很开放,时常穿一件女儿遗弃的衣服风光,好与青年人为伍。 六月里,水大了。沿河支起几张网,顺流漂下几只捉鱼的船。男人们、女人们都快活了。孙头赤裸着上身,精瘦的脊背像块破旧的搓板。他拎着鱼篓,去下网处起鱼,那张网下在顺流处。中午燥热,人们都躲闭了,只有不知疲倦的知了、蝈蝈在大声地吵闹着,唯恐寂寞了这个世界。河水缓缓地流,像是有人推。他顺着路基下来,听得下网处水响,以为网住了大鱼,却见水中一片白光,一个赤身祼体的女人躺在那里。他惊叫一声,逃上路基。 “哈哈。”下网处响起一阵笑声:“孙头,你快下来!”唉,竟是夏婶。 “你这是做啥,快穿上衣服,让人看见!” “大中午,谁看见,我就是让你看的!”说着从水里伸出长长的肥腿。 夏婶的话和动作热得灼人。 我走了!” “好好!”夏婶穿上一个大花裤衩,那窄条的背心紧束着她那丰满而又松驰的胸脯。 孙头把鱼倒进鱼篓,对夏婶说:“捡大的拿!” 夏婶不吭声,却把湿漉的胸脯紧压在孙头的脊背上。 “别逗,让人看见!” “我就给他们看的,我早就是你的人,谁叫你那倔驴脾气,如今快入土了,还装啥体面,下半辈子我伺候你,算还你的债。”夏婶哭泣起来。 孙头拿过衣服给她,劝慰道:“忍几年吧,我们都有隔辈人了,好说不好听,再说孩子们……” “你就这样入土啊!” 孙头望望缓缓流动的河水,嘴唇蠕动了一下,干涩地咽了口唾沫,望一眼夏婶那炽热的目光,低下了头。 “你瞧,河里有个缩头乌龟。”孙头扭转头,夏婶猛得在他皱纹堆垒的脸上嘬了一口,淌着泪,顺着路基走了。 孙头抚着脸上留下的印痕,滞呆呆地望着那舒缓、流动的小河。 夜色笼罩了小镇,铁路上的信号灯变幻着颜色,给寂寞的夜色注进了活力。 孙头拎着两尾鲜鱼,走进了桥头的孔家酒店。店主姓孔,排行老二,镇里人叫他二老孔。他自称是圣人的后裔,供奉着先祖的牌位,说是死后可以和圣人葬在一起,是真是假,无人考究。“文革”倒是沾了他先人的光。人们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念成了在世的孔老二。他矢口否认与孔圣有瓜葛,主动砸了牌位,但在劫难逃,他还是被游街示众,这位“孝子贤孙”差一点见了祖宗。如今却又打出了圣人的招牌,开了这“孔家酒店”。 “孙头,逮住好鱼啦!”二老孔吆喝着把孙头让进里屋,把鱼扔给掌勺的儿子,端上几盘酒菜。“老哥,我这儿有瓶‘芦台春’,这酒是西哈努克喝过的。那年,西哈(他把努克给省略了)到了天津,喝茅台、五浪液不过瘾,愣是灌了一瓶‘芦台’酒。” “如今这酒早倒牌子啦!”孙头烦躁地说。 “这话是实在话,如今啥不掺假,没几个要结婚的大姑娘是原装货。” “别扯淡了!” “好,喝酒!”二老孔端起了酒杯。闺女巧莲端来了菜。那姑娘穿得精薄,轻盈飘逸,画眉涂唇。孙头瞧一眼似罩在纱中的身子,有些痴呆,忙用手遮住眼光。 二老孔夹起一块丢进嘴里,在没牙的嘴里磨着,贴近孙头的耳边:“老哥,凭咱几十年交情,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这话怎么说?” “你也该找个做伴的了,给你叠被焐脚,你瞧,夏婶咋样?”他用手指指对门。 孙头抬头望望夏婶的小院,死一般的沉寂。他摇摇头,叹口气。 “你装啥正经,又不是出家的和尚老道,四十如狼,五十如虎,夏婶那身肉不把你舒坦出屁来。” “你瞎诌什么?” “好,说正经的,你要愿意,我当大媒。” 孙头不言语,猛掫几盅,起身要走,一阵踉跄,险些跌倒。 “你老哥海量,今天咋地啦?”孙头叫唤儿女,搀他进屋。 孙头一觉醒来,发现身边有个女人,他一悸愣坐起来,竟是夏婶。 夏婶给他倒碗茶:“你昨晚喝多了,二老孔说他屋里盛不开,把你送到我这儿,还说让我好好服侍你。”夏婶全没了往日的风骚,羞怯地像个大姑娘。 “玉娘!”孙头叫着她的乳名。夏婶一振,眼里放出光彩。“我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可是难哪!” “难什么,我们又不是青年人,把铺盖卷一并,不就成了。唉,那时候我俩想在一起都不成啊!”夏婶哭泣起来。 “我要和孩子们商量商量。我得走啦,别人看见,好说不好听。”孙头看一眼夏婶,做偷似的乘着夜色溜出了这孤凄的小屋。 回到家,全没了倦意,他打开箱子,拿出一个红布包,打开来,是一对断了的玉镯,在灯下发着幽光,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泪流下来。 那时候,孙头还是个孩子,没爹没娘。经人介绍,在车站脚行下处打杂。那时,夏婶爹是脚行头,孙头整天跟着他转。夏婶爹平时看伙计们动手,有了大件时才露一手。转眼间,孙头二十出头,膀大肩宽,在脚行里挑硬套了。这一天,正装货,忽然看见有辆小驴车拉着个大蒲包,小驴一走三晃。众人吐吐舌头:“足有一千斤吧!”正惊异间,车把式向众人作揖:“各位,这是我们东家要的急件,麻烦了”。众人面有难色。夏婶爹皱皱眉,围着车绕了三圈儿,把袄一甩,勒勒腰带,弯腰要扛。孙头拦住夏婶爹:“您歇着吧,这活还用着您,让给我吧!” 夏婶爹拍拍他的肩膀:“好小子,记住:起身要稳,脚踩八字,用力要匀!”孙头嗯一声。 夏婶爹唤过四个壮汉,搭起蒲包,孙头弯腰插肩,转身跨步,稳稳地上了翘板。众人屏住呼吸,心揪到一块儿。谁料到,孙头刚到翘板中间,只听得“咔嚓”一声,翘断两截。众人惊呼,夏婶爹大吼一声,飞步向前。却见孙头身不动,膀不摇,稳如泰山,那蒲包仍在肩头上。人们惊呆了,那车把式爬在地头磕响头:“真是神仙转世啊!”从此,孙头威名大振。 夏婶那年刚十八,是小镇上的一朵花。引逗得不少小伙子动了邪心,慑于夏婶爹的威名,不敢造次。那夏婶经常去脚行处,目光总是流盼在孙头身上,见此,夏婶爹哈哈一声,并不说什么。 那时汉沽盐场有群“盐驴子。”听说了车站脚行的威名,不服气,派人送来请贴,邀请他们去比个高低。夏婶爹慷慨应允,挑选了十条壮汉,小镇的乡民们在桥头摆下一坛酒,为他们送行。他们来到盐场,见盐坨堆积如山那“盐驴”们经风吹日晒盐水泡,炼就一身骚皮,泛着铜光。他们脱得赤条条,裆处围一条布。双方各出十人,分别装一节车厢,先装完者为胜。夏婶爹微微一笑,双手拱拳:“各位请吧!”那“盐驴”们齐声喝喊,往来如飞,一人扛一包,显得轻松自在。夏婶爹和孙头并不着急,喝足茶水,赤裸着上身,一哈腰,一个胳膊夹一个。对方见状,傻了,甘愿认输。从此,小站的脚行从山海关打到天津没有敌手。 一天晚上,夏婶把孙头叫到家中,爷俩对饮。那夏婶穿了一件东洋旗袍,炒菜布酒。 “孩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您尽管说!” “咱扛大个的,不会客套,闺女看上你啦!”夏婶爹看定孙头。 孙头两眼淌泪:“上子无才无能,只有把子力气,让玉娘跟我受苦啦!”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对玉镯递给夏婶爹,作为订情之物。那玉镯里有一条龙,在水中可见龙游,是孙头的祖传之物。 从此,夏婶便毫无顾忌地与孙头亲近,那脚行的人们也为他高兴。 这车站的日本站长很喜欢中国的古玩。这一天在夏婶家喝酒,他看夏婶腕上玉镯,惊呆了。乘着酒兴,夏婶爹要夏婶把玉镯摘下让他观看。站长愿出一栋日本洋房换这一对玉镯,做为夏婶结婚新房。夏婶爹慷慨应允,夏婶无奈,也只得如此。晚间,孙头来此探望,见没了玉镯,大惊。问明情况,狠狠地给了夏婶一个嘴巴,发疯似地跑到车站,踢开站长室的门。站长正在灯下观赏,见孙头凶神恶煞的样子,慌忙藏到背后。孙头抓住他的手腕,他疼得怪叫一声,手断腕折,玉镯也掉在地下摔成两截。孙头拾起,揣在怀中,回到脚行下处,裹了几件衣服,竟不知去向。 解放后,孙头由部队转业,又回到小镇,当了车站的站长。夏婶早已跟一个姓夏的会计结了婚,夏婶爹也早已得暴病身亡。那时,夏婶虽来车站,但也是相对无言。大地震后,孙头的老伴没了,现在又退休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儿女们回信了,他的心跳得厉害,像一个犯人等着判决。儿子倒是一片孝心:“爸爸,您年岁大了,一个人寂寞、孤独,上我们这儿来吧,有我们伺候。闷了,您去看看电影,您需要什么,我们都能满足您。您找个老伴,别人会笑话我们,说我们不是东西。爸爸上我们这儿来吧!”他叹口气,抓起女儿的来信。女儿是从小娇惯的,说话不讲情面:“爸爸,我想不到您竟提出这个要求,我都感到害臊。就那个夏婶,‘文革’中挂着破鞋游街的那个骚货,让我管她叫妈,丑死了。我明天就回去,找那个娘们算帐!”孙头像被谁擂了一闷棍,晃晃,跌倒在床上。 傍晚,小镇上的人看见孙头拎着个包裹,出了门。 夏婶跑到孙头家,见门上挂一把锁,慌了神,跑到车站上,有人告诉她,孙头坐火车走了。她望望冷落、孤寂的小站,哭了。 几天后,孙头的儿女回到家,见状都慌了。酒店的二老孔交给他们一个纸条。这是孙头临上车交给他,让他转交给他们的。纸条上写着:“我旅游去了……”这个省略号是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清楚。 又过了几天,夏婶也不见了。有人说,看见夏婶在夜间跟一个船家,顺水走了。 至今,他们都还没有回来,成为人们议论的又一个话题。此事被好事者写出来,成为传奇。 、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二级教授、硕士生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唐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理论专著22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等10余部,在《光明日报》《求是》《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省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发表文字多万字。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的《文学理论》《美学》《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刊物全文转载,在《青年文学》《长城》《当代人》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发表文字达多万字。作品获中国文联首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华北区第二届文艺理论一等奖、河北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第十一届、十三届文艺振兴奖、河北省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第六届、第七届文艺评论一等奖、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项奖励,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河北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唐山市劳动模范、唐山市拔尖人才、唐山市模范教师、唐山市首届社科青年专家、唐山市“十佳”青年作家等多种荣誉称号。主播简介:爱的阳光,实名:赵立娟。年生,河北唐山人,机关干部,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热爱本职工作,热爱美好生活,热爱诗文诵读,喜欢穿行在文字与声音里,愿生活处处充满诗情画意。珍惜文化传媒总部组委会: 董事长(创始人):李丽萍~珍惜 副董事长:王玉明 总经理:李天龙~飞龙在天 秘书长:姣姣、风生水起 文学顾问:鲁秋斌、张见秋。 诵读导师:梦、蝴蝶。 总编:小月亮 责编:绿谷 法律顾问:张文凯 山东社长:蕾 河北社长:张辉 内蒙古社长:明月 陕西社长:常浩 山西社长:华子 湖南社长:银莲 江苏社长:邓觐园 黑龙江社长:雪梅 海南社长:李丽霞 广东社长:刘亚飞 上海社长:枝子 北京社长:张文凯 宣传部长:美丽天使、肖丽丽。 珍惜文化传媒总部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ukef.com/nkdl/3686.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军还需继续保卫韩国吗
- 下一篇文章: 大导演们都喜欢什么电影导演片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