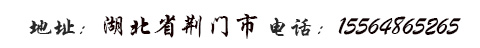父亲生前我最后一次看见的他个人
|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学研究院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文字 /01/19 父亲的葬礼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那些优秀的一面,如同他的死亡一样,我以前从未靠近过,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父亲,这一切存在于生命当中永不会改变。一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 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 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 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 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 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 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 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 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 换句话说,父亲在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在我们每天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这些事始终重复发生着,我现在改变最多的是对于时间的概念。从前时间在我的眼里像可以向前走的一段距离,这道路通向遥远的未来,但愿它的前景充满光明,至少绝不会是乏味无聊的,而现在这里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模式。要是我用一幅画来描述它,应当是在水闸前的一只船: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了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同样的千篇一律。 随着每天的日子过去,当生活触及边沿的一刻便更加怀念以往,那一刻前方之路敞开,生活终于又向前移动。与此同时我在其中恰恰看到了这种重复、禁闭和毫无变化很有必要,它们给予我保护,一旦我离开了它们,所有从前的烦恼便会回来。 突然地,我会被那些所说过的、所见过的、所想过的漫无边际的无数念头完全占据,仿佛又被扔进了从前生活了多年的那种毫无节制、一事无成,常常深陷于自轻自贱和失败的境地之中。往日的憧憬与希望现在依旧同样强烈,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希望的目标在那时可以实现,而不是此时此地。我在这里要寻得另一种目标,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安宁。这里我说的是艺术的生存。 人所知不多,它不会存在。人知道太多,它也不会存在。写作就是从我们所知道的阴影当中把它们抽离和展现出来。这就是写作的真谛。不是那里发生了什么,不是事件过程的展开,这个那里,在其自身。那里,这就是作者的地点和方向目标。但如何让自己到达那里? 我们的思想充溢着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图像,但我们仍然能辨认,充满着我们从未谋面的人,但依旧与之熟悉,而他们是今后我们漫长人生中的旅伴。情感给予我们的是让世界变小,更加自我封闭贴近自我,不向他人敞开,几乎是一种乱伦,虽然我知道这是极度的不真实,因我们其实对什么都一无所知,所以也将难以摆脱情感的困惑。 二这天晚上爸爸穿的衣服有点不般配,不伦不类的。白衬衣或是上衣或不管该他妈的叫什么的上装。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着简单、准确得当,偏向保守。他的衣柜里是衬衫、西服、西装外套,多数是带斜纹的,下装是涤纶的、灯芯绒的、纯棉的,毛衣是羊毛或羔羊毛的。 他属于那种比较老派的教师,而不是不太注重衣饰的新派老师,但又不是旧时代的老派,其间的差异倒不在于此。差异体现在柔弱和强硬之间,体现在试图消除这个距离和试图保持这个距离之间。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当他突然换上一套很文艺范儿的绣花上衣,或是带褶裥的衬衣,像我在这个初夏里看见他的那个样子,要不就是来一双形式很随意的皮鞋,看上去跟许多人一样的很是享受的样子,这展现出的他与实际上的他之间的距离相去甚远,这一点我十分了解。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我自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我反对战争和当权者,反对各种层次的权力机构和所有形式的强权,我不想在学校被填塞得满满的,但我希望我的聪明才智更有组织性;政治观点上我倾向于左翼,世界资源的分配不公让我想要爆粗口,我希望在分配社会财富上人人有份,那么资本主义和财阀统治集团就是死敌。我的意思是说所有人的价值都是均等的,而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比他的外在要重要得多。 换句话说,我赞成深度反对表象,褒扬美反对恶,支持弱势反对强势。这么说我应当高兴才是啊,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走到柔弱的这一边? 不,这只是柔弱的外观表象,就是说这圆框眼镜、灯芯绒裤子、合脚的鞋子、针织毛衣,这些让我感到几近鄙视了,因为同我的这些政治观念并存的还有其他的观念。 与音乐紧紧联系的意念,在那个世界里完全是以另一种尺度来衡量什么是优质,什么是酷,总是准确地同我们生活的时间紧紧绑在一起,要表述的将是这个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与当时的劲歌排行榜飙在一起的那部分,不是柔和的色彩和发胶的魅力,因为这些都是与销售有关的东西,与外观展示和娱乐相关的东西,不,应当表现出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又不失传统意识;有深切感受又不乏灵巧活泼;聪颖睿智但又简单直率、不装腔作势。 真正的音乐不是为所有人的,不是最畅销的,但它仍然表达着一个时代,我的时代,我的经历与历程。啊,全新的时代。我站在新时代的一边。 回声与兔人乐队的主唱伊恩·麦库洛奇(IanMcCulloch)在这种思想体系里是位先驱。大衣,军夹克,篮球鞋,黑色的太阳镜。这与我爸爸的绣花衬衣和萨米靴相去甚远。 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无可厚非,因为爸爸是属于另一个年代的人,想象着那个年代的人将开始像伊恩·麦库洛奇那样着装,开始听英国的非主流音乐,很在意发生在美国屏幕上的事情,追随R.E.M.或GreenonRed的首张专辑,再不就出现把牛仔饰带混杂于衣柜间诸如此类的事,这几乎是个梦魇。 重要的是这有绣花边的衬衣和萨米靴本就不是他。可他依旧要以这种面目悄悄流入这个圈子里,仿佛进入某种无章法和茫然无知之中,几乎就是一个娇弱女子,如同他完全失去了自我。甚至他嗓音里的那种强硬也消失了。 回声与兔人(EchoTheBunnymen),年代新迷幻(neo-psychedelic)领头乐队,图为乐队主唱伊恩·麦库洛奇(IanMcCulloch)。这个家庭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但谁都对这些事只字不提,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就像某个地方的宣言,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处于大家共同造就的这种气氛中……我总是注视着人们之间发生的事,试图从中找到答案,很久以来我也认为,在观察其他人的方面我很有远见,但并非如此,我到处看到的只是我自己。 没有哪一天的天空不是充满着奇幻无比的云彩形状,被光照耀下的每一朵云都各具一格,千姿万态,绝没有重复的形式,因为人们始终是看着它们的,而变得了熟视无睹,所以我们过着的生活中已没有这不停变幻着的天空,也便不去想它或是看它了。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用拇指抹去挂在瓶口的一滴酒,把手指头放进嘴里舔干净,这时候在桌子另一端的祖母正把一盒烟丝打开,捏起一些放进了卷烟机里。因为无论这最后的几年里她过的是一种多么可怕而难以忍受的生活,但这一切只是她所经历过的困难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当她看着爸爸的时候,在她的眼里他是婴儿、儿童、少年、成年男人,他所有的性格特点和所有的个人属性都凝聚在这一瞥当中,她看见他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她的沙发上拉屎拉尿,那是短暂的一瞬间,她那么衰老,较之她多年积攒的与他共处的许多时光,这不足以组成一幅画像。 我想,这房子也是一个同样的例子。最早的有许多酒瓶的那房子本身就是一个“酒瓶屋”,而这栋房子就是她的家,一个在她这里度过了自己最后四十年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酒瓶,再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意义。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我一直都在哭泣。当我在那儿走着,在那里锄草的时候,一股股的浪潮穿透过我的全身,我已无能为力加以抵挡,泪水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在十二点钟的时候英韦在阳台上叫我,我走进屋去和他们一起吃东西,他已经把茶和圆面包放到了桌上,祖母总是招待我们吃圆面包,在电炉盘上的铁丝板上把它烤烤热,这样原本是松软的面包皮就变得硬脆了,当牙齿一咬在上面,大块的面包皮散落下来,但我不饿。 所以很快地出去了想继续干活。独自一人走到外面的花园里是一种自由和释放,也有成就感,因为工作的成效立时可见。天幕已经关闭,挂在那里的灰白色的云层就像是罩住下面的一个盖子,显现出暗黑的海面与这清澈透明的反差,这城市,在这敞开的天穹之下,只不过像是一小群微不足道的房子,一泡吐在地上的、变得了更加厚实和坚固的唾沫。 我就站在这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因为我的目光大多数是投向那转动着的刀片上的,草叶就如士兵般纷纷倒下,绿草不多,更多的是灰色和黄色的草,间或也夹杂一些浅红色的毛地黄花和金黄的太阳帽花,我有时候也抬起头来,望着天空那一望无际的浅灰色的被盖和海洋辽阔无边的深灰色地板,望着码头上的一片忙碌和混乱,船檐和船体,桅杆和舰首,集装箱和褐色的锈迹斑斑的铁件废物,望着那座具有自身的色彩和韵律的城市,犹如机器一样地在颤抖着,望着所有这一切,此时的我泪涌如泉,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为了爸爸,他是在这里长大的,他死了。 或许我也不是因为这个而掉眼泪,或许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因,或许我把这过去十五年里的悲伤和痛苦都聚集在了自己身上,现在把它们宣泄出来。这没有什么要紧的,没什么事情是要紧的,我就在那花园里来回地走着锄草,这些草长得实在太高了。 我站在英韦的身旁,就在父亲的跟前。他的脸颊是红色的,就像被血浸泡过的那般充盈。这一定是当他们试图擦去血迹时血得以留存在了皮肤的毛孔里。还有他的鼻子,鼻梁断裂。但虽然我目睹了这一切,却仍然是视而不见,因为有关他的所有细节都消失在了其他的更广泛的层面当中。 他那些优秀的一面,如同他的死亡一样,我以前从未靠近过,对我来说,他是一个父亲,这一切存在于生命当中永不会改变。在我目送英韦开车向斯塔万格的方向驶去后,在我走回祖母的房子时,首先我想到的就是那些血。那里怎么可能弄上血的呢? 祖母说过了,她发现他是死在椅子上的,除了这个信息之外最能让人相信的就是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或许正发生在他睡觉的时候。然而殡仪馆不只是说有血,而是说有很多的血。还有鼻子,鼻梁断裂了。所以在他被发现的那里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 他是否是站起身来,在剧痛里,撞在了壁炉的砖石上?跌倒在了地板上?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墙上或是地板上都没有任何血迹?怎么可能会祖母没说到有血的事?因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仅仅是血这类东西,让他不可能静静地入睡。她把那些血迹擦洗掉,然后全忘记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没擦洗什么东西也没把什么东西藏起来,在她身上看不到有要这么做的必要。同样奇怪的是我把这事也很快地忘掉了。 啊,或许这也并不奇怪,现在要涉及的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样一回到祖母家我就得马上和英韦通话。我们必须要和负医院的大夫联系上。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当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三我看着下面路上延伸开去的住宅区里那一片房子的屋顶,想到了十六岁时的我在夜里是怎样在它们中间穿过,心里充满的那些情感的起伏剧变。 于是我看到了的那一切,甚至是花园后面一个生了锈的、歪歪斜斜的晾衣架,甚至是一棵树下的地上那些腐烂的苹果,甚至那条被篷布包裹起遮挡好了的船,和那伸在外面的湿漉漉的支架,船底下那些发黄的,扁平的草,都是辉煌般的美丽。 我看见马路的另一面那些建筑物背后的草坡,想到了一个蓝色的、凛冽的冬日我们曾和祖母在那里乘雪橇滑下坡。在阳光照射下的雪是湿润的然而又是那么刺眼,像是在高山上的那种强烈光线,位于我们下面的城市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的,把在那里发生着的事情完全敞开来,在我们下面的街道上走过的人们、驶过的车辆,路的另一边在一家当地公司外那个在车道上扫除积雪的男人,其他的小孩子都在坐雪橇玩,仿佛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聚会,就单单在天空下的这里兜着圈子玩。 当我在往下走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所有这一切包裹着我的环境都进入了视野同时让我思索,但这只是流于表象的,只是在意识里最外的一层,因为爸爸死了,这让我在心中感到悲痛,这种情绪辐射到我所有的思考和情感里。 在这些个回忆里也能找到他,但他在那里面无足轻重,这一点着实令人奇怪,在那里有关他的什么念想都没有。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在70年代初期的一次,爸爸沿着人行道走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我们去小卖店买烟斗清洁器,然后要去祖母祖父家,他扬起下颚仿佛同时他对自己发笑,我知道他的这种快乐,还有就是爸爸在银行里,他一手拿着钱包,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把头发往后拨,在柜台跟前的玻璃上看着自己发光的身影,要不就是爸爸坐进汽车把车开进城:在这些回忆中我没有感受到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这就是说,我回忆的当时,我有感受,而不是现在,在我想着它们的时候。带着他已经死了的这个念头,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在这个念想里,他就是一切,这很自然,念想也是一切,因此当我去到那里时,在一个飘着轻轻的、蒙蒙细雨的日子里,好像发现自己进入另一个天地。居于这个天地之外的没有任何意义。 我在看,我在想,然后我所看和我所想的又已然退去:这跟它们没干系。跟什么都没干系。只有爸爸,他死了,仅仅和这有关联。 我朝墙那里迈出了几步,摇晃着手里拿着的东西。他的戒指、首饰、几枚硬币、一根针。就这些。这些东西本身看起来只可能是些平常的日用品。 但是他把它们带在了身上,那戒指一定是戴在手指上的,首饰是戴在脖子上的项链,当他死了之后,就给它们罩上了一种特殊的光环。死亡和黄金。我把它们在手掌里一个一个地摆弄着转圈,它们让我心里充满不吉祥的感觉。我站在那里对于死亡的恐惧就跟我在小时候那会儿对死的恐惧一个样。不是因为我自己会死,而是对那些死者。 我把这些东西放回了信封里,再把它放进我的衣袋里,在两辆汽车的空隙间跑过马路,进到小卖店里买了一份报纸和一块狮子巧克力,我吃着巧克力走完了通往那栋房子的最后的几百米。 我写出了一本给我父亲的书。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如此。这本书就是为他写的。我放下手里的书稿,站起来,走到了窗边。 他对于我真有着这么重大的意义?啊,是的,他就是这样。 我希望他将会看见我。 我第一次明白了我写作,确实是为着什么的,不仅仅是为了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装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写到有关我爸爸的一个章节时开始哭泣了。我一写到爸爸泪水就沿着脸颊往下流,让我几乎看不清键盘或是屏幕,只是敲打着字符。当这些伤痛已经在我身上消失后,我感觉不到它曾经的存在,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寻到它。 我的父亲是个蠢货,一个我不想与他有什么干系的人,和他保持远距离对我来讲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了。这里说的不是保持距离,而是根本就没有他,他的什么事也触及不到我。一直就是这样的情况了,然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写着,眼泪哗哗地直流。 我又坐在床上,把书稿放在膝盖上。 但这里面还有更多。 我也想显示出我比他出色。我比他强大得多。或者就只是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他将会为我而感到骄傲自豪?真正地认识我? 他从来不知道我将会出版一本书。在他死之前,我们最后一次的单独见面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他自然是又问起我那段时间在干什么,我回答他我刚好开始在写一本小说。 我们走上了女王街,出去吃晚餐,虽然天很冷,汗水却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问话的时候,并不看着我,他问这书将会怎么样,一次非常明白清楚的谈话。我点着头回答说有一个出版社对此很有兴趣。当我们走在路上时他向我投来的那一瞥的样子,好像他还继续待在某一个他曾经待着的地方,或许他可能还会在那里。 “你干得不错,很好,卡尔·奥韦。”他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对这个记得很清楚?通常我把人们对我说的一切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管是多么亲近的人,在那种情势下没有任何的征兆显示这是我同他在一起那些日子里的最后一次。 我记得或许是因为他使用了我的名字,我听到他最后一次这么叫我应当是四年前的事了,出于这个原因,让我感到和他有意想不到的亲近。我记得或许是因为就在当时的几天前我写到了他,直率地写出了与他现在向我示好的态度完全大相径庭的感情。 或许我记得是因为我痛恨他把我攥得紧紧的,显而易见,我很高兴我还是小孩。在这个世界上我绝不会为他的缘故去做什么,为他的缘故去受人指派干什么,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因素。 现在这种意愿已全无意义。 四我把这摞书稿放到床上,笔放回了箱子的插袋里,弯下腰从旁边的地板上拿起那个纸盒,试着想把书稿再放回去,但放不进去了,于是我就把书稿放回箱子里的老地方,在箱的最下层,仔细地用衣物把它盖上。 那个放在床上的纸盒,我站在那里长久地盯着它,每一次看着它的时候,对小说的诸多的想法便有了头绪。拿着它下楼把它扔到厨房的垃圾袋里去,这是我最初的冲动,进一步想想这不行,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把它搅和在这栋房子里。 于是我又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到一边,把纸盒放在箱底书稿的旁边,上面盖上衣物,放下箱盖,在走出房间以前,把箱子拉链拉上。 爸爸尸体的画面让我对食物感到恶心。但一杯茶很难会让人联想到死亡吧?我在电炉上用一只平底锅烧水,把茶袋放进冒着热腾腾水气的杯子里,站在那里看着那颜色怎样在茶袋里释放出来,慢慢地旋转着地流失在了水里,直到水完全变成了透明的黄颜色,我端起杯子拿着它走到了外面的阳台上。在远远的海峡口处丹麦的海洋游轮发出停泊信号驶进了港口。 在黑暗的天空中,仍旧能看到一抹蓝色,给人一种材质的感觉,仿佛它实际上就是一方巨大的桌布,我也看见了星星,就像是穿透千万个小洞里发出的光芒,它们是从背后的光线里派生而出。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我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在窗台上。我又想起来那个晚上我父亲更多的事情。人行道的地面上有了较厚的冰层,东面吹来的风穿过街道一扫而过,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我们走进了一家饭店的餐馆里,把外套脱下挂上,在一张餐桌旁坐下。爸爸呼吸沉重,用手在额头上一抹,拿起菜单来看,他的目光在菜单上从上到下扫视一遍。又开始从上方起再看。 “看上去这儿好像不卖酒。”他说,站起身来,走到餐厅主管那里。他对他说了些什么。当那人摇头时,爸爸转身走了回来,几乎是一把抓起了挂在椅背上的外套,穿上它同时朝门道走去。我急忙跟在了他身后。 “怎么啦?”我说,那时我们已站在了外面的人行道上。 “那里不卖酒,”他说,“我的天,这是家禁酒的饭店。” 然后他望着我笑了。 “我们吃饭得要喝酒,你不明白呀。但不要紧。这里直走下去有另外一家饭店。” 我们在苏格兰人饭店前停下,在窗边的桌前坐下后,各自吃自己的牛排。应该是说,是我在吃牛排;当我吃完以后,在爸爸餐盘里的牛排几乎没动。他点燃一支烟,把最后的一点红酒喝下,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说他计划着要开始当一名长途货车司机。 我不知道对此该如何应对才好,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当个长途货车司机是很不错的,他说。他一直喜欢开车,喜欢旅游,现在有机会做这件事还有人给你报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他说。是呀,这是个好工作,我说。 但现在我们就到这里吧,他说。我结账。你只管走。你肯定还有好多事要干。看见了你我很高兴。我按照他说的做了,起身拿起夹克,对他说再见,然后走进饭店的大堂,走到外面的街道上,有一瞬间的踌躇,是不是要打车回家,最后决定不坐出租,朝公交车站走去。 通过窗户我又望见了他,他正穿过那一带的酒店街区,走向街另一端的一道门,那里直通酒吧,我又看见了他走动着的身影,那庞大沉重的躯体,是那样的匆忙和急不可待。 约瑟夫·寇德卡摄影作品这是他生前我最后一次看见的他。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始终是他在端正形象尽量律己。在这两个小时里他用尽所有的力量在克服自己,努力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不心神恍惚,将身心都集中一处,做一个他曾经就是如此的那样一个人。 这个谈话让问题解决了,我心里感到松快,走到花园里继续锄草。天空中高挂着白云,日光柔和,空气温暖。我在两点钟结束工作。于是进屋对祖母说我要去会一个朋友,换好衣服后我奔那个小教堂去了。 小教堂进口处的外面停放着同样的一辆车,当我敲门后给我开门的是同样的一个人。他向我点点头,打开了前一天我们进去过的那间屋子,他自己没有进去,我又站在了爸爸跟前。这一次我有思想准备,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等待着我,他的身体,皮肤在过去了的这一昼夜里一定是变得更加暗黑了,再没有唤起我前日里的那种撕裂心肺的情感。 现在我看到的是没有生命的躯体。这曾经是我父亲的那个人和他躺着的这张桌子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这张桌子所在的地板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窗户下面墙上的插座不再有任何区别,或者和旁边的台灯一段垂落下的电线不再有任何区别。 因为人只是在所有其他形态当中的一种形态—如造物世界一再显示出的那样,不只是当其有生命的时候,也包含那些生命不再的物质,以沙土、石头和水的形态而存在。 死亡,像我始终感觉的那样,在生命里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幽暗而令人销魂,它如爆裂开的一根水管,风中折断的一个树枝,从衣架上滑落坠地的一件衣衫。仅此而已。 摘自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VOL.1父亲的葬礼》工作室汇集一批资深史学者、记者、编辑、 作家、教师、导演等专业人才, 竭诚期待与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用心凝练成文,量身定制版面, 拍摄独家视频,留住珍贵家史, 最终为您奉上精美的家史传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ukef.com/nkdl/7531.html
- 上一篇文章: 德甲推荐柏林赫塔VS拜仁慕尼黑,首都行善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